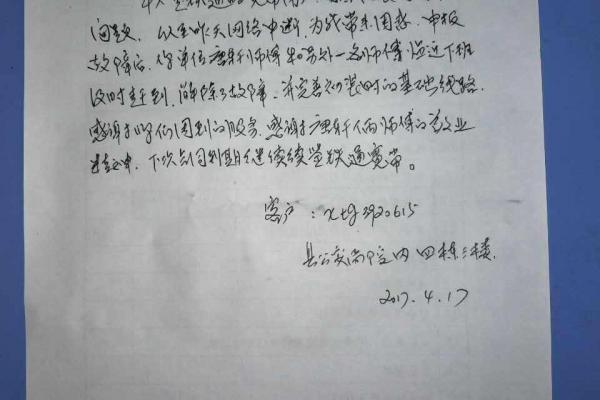晨光未透窗玻璃时,键盘已与第一声汽笛奏响二重奏。一万五千个黎明的仪式里,稿纸在敲击声中生长出字符的骨骼。
四十三载铁路生涯,给了我铁味的文字。键盘脆响是钢轨的回声,老工长汗湿的背影、老张马甲松脱的第二颗纽扣、老李安全帽里泛黄的家书——这些细节在稿纸上苏醒,像道钉般铆进记忆。退休老工长带走的老式道尺,丈量过他说的真理:“我们测的不是1435毫米轨距,是思念的伸缩缝。”这句话成了我所有文字的轨枕,托起等待与目送的永恒叙事。
我的键盘始终与钢轨保持平行的虔诚。两根冷光钢轨是大山摊开的五线谱,我的文字是跃动的音符。写作如道钉入枕木的仪式,把流动的光阴锻造成金属记忆,让道砟间的汗珠折射出银河的碎钻。
四季在钢轨上轮回,我用文字为山区铁路写生:春描道砟间蒲公英绒毛的白,夏摹探伤工后颈古铜色的经纬,秋捕桥隧工雨衣上滚落的乡愁雨珠,冬刻除冰人睫毛凝结的冰晶星座。这些文字是滚烫的心跳,是钢轨里暗藏的裂纹——我渐渐懂得,写作该像钢轨探伤仪,在平整生活下叩击细微的动人。
此刻键盘与钢轨共振出奇妙通感:岁月的痕迹是轨缝预留的伸缩量,段落空白恰如1435毫米的轨距。我既是线路工也是文字匠,用键盘的探伤仪检查词语的平顺度,拿修辞的轨距尺校准情感的几何尺寸。
泛黄的剪贴本里,藏着文字与铁路的共生史。绿皮车时代的篇章带着煤烟味尾音,像生锈螺栓需慢慢拧开;电力机车时代的段落则如无缝钢轨般流畅,标点符号都成了接触网整齐的吊弦。这蜕变教会我:执笔的手终将被时代握着写,正如钢轨终会被车轮重塑轮廓。那些写在时刻表背面的诗、夹在调度令里的散文,早已成了钢铁动脉最软的心电图,记录着一个时代奔跑的体温。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