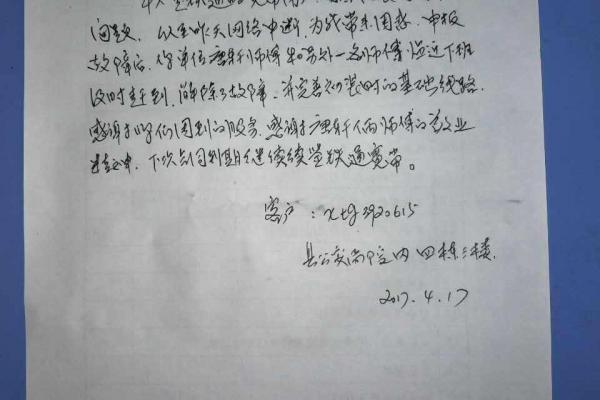清晨七点半,放满工具的车间还没完全苏醒,牛琦牛师傅的工具箱已经“咔嗒”一声落在了工位上。蓝色的工作服前襟沾着昨天没洗干净的油污,像缀了几片深色的勋章,他弯腰从工具箱里掏出卷尺,对着刚刚报活的架车机,先绕着走了两圈。
“老伙计,又哪儿不舒服了?”牛师傅拍了拍架车机外壳,指尖划过冰冷的金属表面,像是在给老朋友诊脉。昨天值班的同事说这台机器主轴转起来“嗡嗡”响,还时不时卡壳,可他凑近听了半天,只听见通风口微弱的风声。他没急着拆零件,而是蹲下来翻出架车机的保养记录,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记着每次维修的日期和故障原因,最后一行停在三个月前——“更换轴承,运转正常”。
“说不定是轴承又松了。”牛师傅起身,从工具箱里拿出内六角扳手,拆开机器外壳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机油和金属碎屑的味道涌了出来。牛师傅眉头没皱一下,反而凑近了些,眼睛盯着里面错综复杂的齿轮。阳光从车间的高窗斜射进来,照得他鬓角的白发格外明显,也照亮了他指尖的动作——左手扶着齿轮,右手握着扳手,顺时针转半圈,又逆时针回一点,动作慢却稳,像在摆弄一件精细的工艺品。“拆零件不能蛮干,就像给人做手术,得知道哪儿能碰,哪儿碰不得。”他常跟年轻的工友这么说。
修到一半,车间的电话响了,是:“牛师傅,车床的输送带卡了,床子还在旋轮呢1牛师傅应了声“马上到”,把没拆完的零件小心地摆在泡沫板上,每个零件的位置都跟图纸上一一对应——这是他几十年的习惯,从不会让零件“迷路”。
输送带旁,几个年轻工人急得团团转。牛师傅走过去,没先动手,而是让他们把电源关掉,自己则趴在地上,顺着输送带的轨道看过去。“是滚轮卡住了,里面缠了根铁丝。”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螺丝刀,伸进滚轮缝隙里,一点一点把铁丝勾了出来。前后不过五分钟,输送带重新转了起来,负责旋轮的老王拍着他的肩膀说:“还是你行,我们看了半天都没找着问题。”牛师傅笑了笑,擦了擦手上的灰:“别急,慢慢来,机器跟人一样,有脾气也有规律。”
回到自己的工位时,已经快中午了。牛师傅的眼睛还盯着那台没修好的架车机。下午,他换了新的轴承,又给所有齿轮上了油,开机试了试——“嗡嗡”声消失了,架车机运转得平稳又顺畅。他满意地点点头,在保养记录上写下今天的日期,又加了一句:“建议下月检查齿轮磨损情况。”
傍晚六点,车间的灯陆续关掉,牛师傅最后检查了一遍自己的工位,工具箱里的扳手、螺丝刀摆得整整齐齐,地上也扫得干干净净。走出车间时,天边的晚霞正红,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想着给老婆跟孩子唠唠家常,讲讲今天的事。
有人说机修工的工作又脏又累,可牛师傅不这么觉得。他手里的扳手拧紧的是故障,身上的油污见证的是责任——那些在他手里重新运转的机器,是工厂的心跳,也是他日复一日守护的“伙伴”。在扳手与油污的世界里,他用自己的手艺,让平凡的日子有了沉甸甸的意义。(龚昱康)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