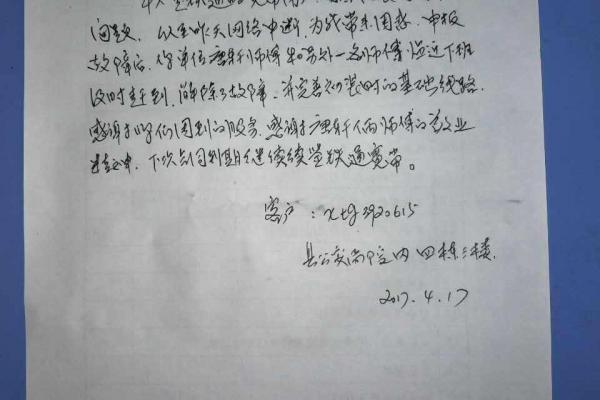“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首歌未必广为传唱,但大凡听过这首歌的必会记住这句歌词。只是,记住归记住,终究没有谁能说得清弄得明“情”到底为何物?
爱尔兰诗人叶芝在《布朗·潘尼》里这样写道:“爱是个难题∕再聪明的人∕也无法探知她的蕴涵。”
是的,即便再聪明的人,也无法告知我们“情为何物”。更何况,当人们深陷于爱情之中时,没有谁是聪明的。
事实上,爱作为人类感情中最复杂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从来就是难以界定的,尽管它对我们的生命有着巨大而神奇的支配力。这种巨大而神奇的支配力表现在:它既有创造性又有毁灭性,既美丽又令人望而却步。诺亚方舟可以载我们到梦想的伊甸园,也可以将我们搁浅在痛苦的沙滩上;当失去曾经拥有的感情时,我们常常沉湎于悲伤之中而不能自拔。
一旦涉及到最深刻、最难以界定的感情时,我们总是希望诗人或艺术家能提供生动的表达和形象的描绘。但很少有散文能精细表达出恋爱时陶醉的感觉,虽然一些抒情诗几乎接近于此。实际上,每种爱的私语,都几乎很难分析和剖析它的含义。
正如卡夫卡形容的那样,爱就如纺织的陀螺,它一旦停止转动,就失去了魅力。
爱情的确是一个不好述说的东西。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不只被我们所熟知,还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长达几个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但丁和彼特拉克也颂扬这“高级”形式的爱。彼特拉克用宗教敬拜的语句来描绘他的恋人劳拉:“她是催人奋进的源泉,是指引我们通往天堂的正确道路。”
永恒的精神之恋这一概念,在19世纪重新被列为文学主题。从那以后,它就再也没有从文学中消失过。精神高于肉体的最极端形式,就是恋人们为防止热情的消亡而对同月同日的死的追求。比较人道主义的观念认为,完美的爱情是肉体和精神的结合。
而世俗之爱,俗就俗在只有性,即肉体。世俗之爱的发展路径,大致如下:恋爱—性—婚姻—家庭—孩子。这般简洁明了、目的单一的爱,就是为了找个伴,结束他们的单身生活,也一并摆脱了各自的孤独——如此而已。
柏拉图的精神之恋,未免太高雅,尽管也很令人神往,只是实在无人能及。无人能及,说白了,就是我们做不到。当然,这样说又有些过于绝对了。世间终究也还是有这样的人的,比如中国的哲学家金岳霖,大抵是能够算一个的。
不管世俗之爱何等简洁、又何等单一,但我们依然要维持这种爱。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世俗之爱,人类怎么繁衍下去呢?
倘使肉体和精神的结合,是一种完美的爱情,那这种爱情也依然只能为极个别人所拥有。实际上,世俗之人所谓的爱,只能有肉体之欢这唯一的一种形式。
这样的爱情,也很能说明一种现象,或者叫做一个问题。这种现象,亦即这个问题,就是:许多人从结合到分离,固然并不完全都是由于那些沉湎于肉体关系的人对这种关系产生了厌倦,并最终失去对人的爱恋,但你还是不得不承认:一大部分人的婚姻破裂与他或她爱上了另一个她或他有关。
世俗之爱,简洁、单一,一点也不复杂。爱一个人就爱呗,然后就是性,就是婚姻,就是家庭,就是孩子,如此不复杂的爱情,未必就能让两个人的这种爱走到尽头。某种程度上,正是他们缺乏对爱这种复杂性的认识,想得过于简单,才使他们的爱和婚姻变得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尽管离婚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般简单。
世俗之爱,结合的时候,肯定是缘于性;而分离的时候,大多又是缘于性。可见,爱,若只为了性,不会走得太远。
可他们不为了性,又能为了什么呢?肉体和精神相结合的爱,不要说他们做不到,即便那些自以为高雅的人,浪漫的人,又有几人获得了这种爱?这种完美?
爱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何要爱?这些问题若追索起来,真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索姆·格思把恋人比做嬉戏中的动物。这一形象的比喻显然比任何纯理论书籍更易于人们理解爱是如何降临到这个世界的。索姆·格思这样写道:“在一片由欲望驱使下开辟出的旷野里,一群热情美丽且皮肤光滑的动物在自由嬉戏。”索姆·格思的比喻让我想起马丽华在《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一书里写下的一段文字——
藤蔓掩映中有个山洞,一只成年母猴在此栖居,有关它的来历我们不知其详,讲述故事的老人没有提到。总之,如同早已注定了的那样,存在仿佛就为等待。此时母猴在暗处已经望见了采食的公猴,但心怀疑虑,不知对方是友是敌。小公猴也发现了山洞,同样心存犹疑,但禁不住葡萄的诱惑,仍在每一天匆匆去来。终有一天,母猴现身。公猴定睛一看,眼前的异性同类貌美如花。接下来,公猴鼓足勇气说了,让我们一起生活吧!母猴满心欢喜地回答:我已等待很久!
讲故事的老人说,这个故事在雪域西藏流传下来,是猴子变人神话的最初版本。可我却把它解读为人在成为人之前爱情的“最初版本”
而柏拉图在他的著名的专栏文集中,以其幽默风趣的口吻,运用性神话诠释了两性之爱的不同形式。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则宣称,人类最初可被分为三类,他们均有双倍的脸庞、肢体和器官——双倍可以是雌—雄的、雄—雄的或是雌—雌的。直到有一天,上帝宙斯因恼怒于他们傲慢的自信而把他们一分为二。于是,从那以后,受苦受难的男男女女们就开始了找寻他们丢失的另一半的工作,不管那个另一半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寻爱从根本上来说是渴望团聚的过程,是为了与自己的另一半结合而使自己不再孤独。有些恋人的结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那是因为那些人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柏拉图滑稽的故事中确实包含着人类爱情的基本真理,那就是:人类寻求爱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摆脱不满足感。英国浪漫诗人塞姆·泰勒·柯尔律治将这种情感描绘成“用自然界最完美的方式,使整个生命为了达到圆满而与另外的某个生命相结合的渴望”,爱的经历往往被注入了类似于怀旧的渴望,就仿佛我们有一种感应,早在某个前世中就经历过一场完整的爱一样。又一如那一只母猴满心欢喜般地回答:我已等待很久!
19 世纪的哲学家叔本华认为,“物种天才”使我们心甘情愿地服务于下一代,并自欺欺人地认为那是在取悦自己。他还认为,爱是与情欲不可分割的一种情感,是它,使我们不断繁衍后代;也是它,引导我们去寻找与自己性情相投的人,但无论如何,它基本上保留着一种个人性冲动。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