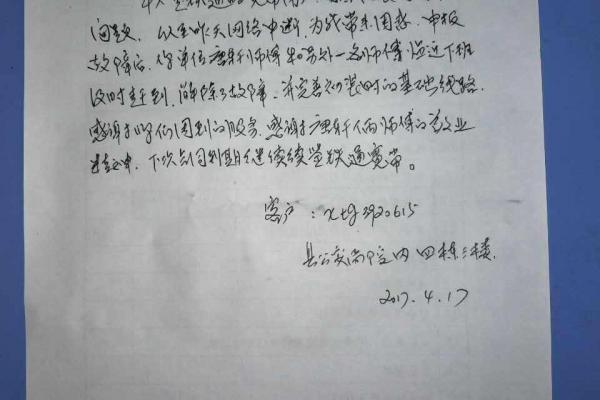“安静得如同陵墓”,这是一个名作家的一部小说里的一句话。我对这部小说的记忆并不深刻,但对陵墓里的那种安静感,却较有体会。当然,这体会来自于我时常去父母的墓地。
对活人来说,除了约定俗成的节日,一般情况下没有谁会喜欢往墓地里跑。活人有许多的事要做,每个人都忙得焦头烂额,何况墓地是死人的所在,即使有我们的亲人在,也不必要老往那里跑。
相比他们——那些忙碌的人们,我则很有时间,很闲适。我的时间除了读书,还可以不时地跑跑墓地。
跑得久了,感觉墓地里的亲人并没有远去,他们依旧生活在我们的时空里。从我居住的城市驱车来到墓地,不过四十分钟的时间,就好比去城外的亲戚家串门。我的父母就住在城外的乡村里,作为儿子时常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岂不是很应当的事吗?
不同只在于,父母在世时,我会端个凳子坐到他们面前,而如今,我只能席地而坐。墓碑上有父母的像片。我母亲的像片是她60岁时照的,这张像片一直存放于我的书房,每天我都与母亲相视几分钟。母亲长得很漂亮,我的朋友们见了我母亲的像片时都这么说。我也认为我的母亲很漂亮。父亲的像片是他50岁时在杭州拍摄的,这张像片上父亲留着短发,同我现在的发式相当。
我把我喜欢的这两张像片交给了墓地管理处,他们把像片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原模原样地制到了墓碑上,我看了很是欢喜。
每回去看望父母,我总要给母亲带上一束花——母亲特别爱花。小时候很好奇,生活得并不很好的我们,却总可以看见家中柜子上一只空瓶子里插着好些不知名的花,那是母亲从田间采摘来的。哥哥也很好奇,只是他比我有心计。他问,妈妈,这花要是能吃多好啊!母亲明白哥哥的意思,她没有直接回答哥哥的问题,而是说,生活是艰苦了点,可再怎么艰苦,人也不能失去生活的情趣。母亲说这话时的那副神情,直到今天依然深深地镌刻于我的脑海里。
然而,当我参加了工作,有了工资后,我买了第一束花献给母亲时,母亲却不高兴。我纳闷了:妈,你不是喜欢花吗?她说,妈是喜欢,可不喜欢花钱买的花。你看,我们家里的这些花,都是我自己去采摘的,这样的花,看起来才叫人心里舒服。
父亲爱抽烟,这是他一辈子惟一的嗜好。母亲年老时,咳嗽厉害,父亲就跑到院外去抽。而入夜后,父亲则从来不抽,他怕影响母亲的睡眠。
席地而坐后,我会给父亲点上一支烟,再给自己点一支。父亲的那一支燃烧得很厉害,我笑说,爸!是不是好久母亲不让你抽烟了?还是担心母亲咳嗽,怕影响母亲歇息?父亲不言,可他嘴角的笑意却仿佛在告诉我,他很开心我能常来,并与他一起抽支烟,说说话。
我常到墓地来,的确是因为担心他们孤独。许多回梦境里看见父亲一个人立在门口,没有看到母亲。醒来后,心里酸酸的,便立马起床,不管这一天有什么样的工作,我也不管不顾,径直赶往墓地。有时候,我会在那里呆一个上午;有时候,我会在那里呆一个下午。有一次,下了雨,天迅速地黑了下来,我从墓地急急而出。当时非常惊恐,忽听见有人叫我乳名——由于惊恐,明明那个声音非常熟悉,可我就是想不起。直到好多天后,我才想起这个叫我的人是九叔。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也葬在这里。
去年的这个时节,我在墓地里与一个牧羊老人相遇。他说,不年不节的,你来这里作甚?我笑而不答。他说,你的心思我懂,你是怕你的父母孤独。我站起身递给他一支烟,又给他点了火。他抽了一口,蹲了下来。说,你父亲叫业茂吧?我说,是。他说,茂哥是个很好的人,俺与他很早就熟悉了。我登时想起了原先那个看墓的人。我问他:“看墓的……”,不待我话说完,他就说,看墓的人和你父亲也是好朋友,去年死了。他用手指了指墓园的东南角,说,他就葬在那里。我有些感叹,说,看他的身体挺好的嘛!他说,好什么好啊,浑身都是玻不过,他并非死于病,而死于他那张嘴。我笑了。他说,你别笑,你觉得俺是在说笑话吗?俺说的可都是实话。他那张嘴啊一辈子就爱胡讲乱讲,惹了不少是非。人这嘴巴就是为了吃饭,吃饱了就闭上。可他不是这样。吃饱了就讲得更厉害。话说得太多了,死神是不高兴的。当然,最不该的,是他把墓地里的一些鬼事也成日到处传讲。俺对他说,这些话你还是少说,他不信,结果就死了。
老人很有意思,一个人以放羊为生。那天他心情很好。他说,他的心情每天都好。我再给他烟时,他拒绝了。他说,俺抽不习惯。他掏出烟袋,说,这东西过瘾,你也来一口吧。他用手重重地一撸,说,俺没病,抽吧。我吸了一口,立马被呛了一下,我苦皱着眉头,说,不行不行!我也不习惯。他说,你父亲抽的习惯。说完,他把烟袋放到了我父亲的碑前。他说,你来看,你看你父亲多么喜欢抽我的烟!我低下头,果见那烟袋锅一闪一闪的。我有些感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却说了,你怕你父母孤独,其实恰好说明你比他们还孤独。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世间像你这般不年不节的也跑来看父母的,难得一见哪!俺早就注意到你了,可俺不愿意打搅你。俺只想告诉你,来看看就可以了,不要流眼泪。做男人要坚强,要像你的父亲那样,勇敢面对人世间的种种不幸。你要知道,你一流泪,你父母就会误以为你在这人世间活得不愉快,他们一心疼,就有可能会把你带走。你还年轻,还有好多事要做,我看得出,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有想法,你不能走。
他不让我流眼泪,可我的眼泪却在不知不觉间流了下来。老人见状,忙不迭地“唉唉唉唉”地责怪起自己来:瞧俺这张嘴,叫别人不要乱说,自己竟胡咧咧了。他递给我一片柔软的树叶,说,擦擦眼,俺带你看看俺老婆子的墓。
他老婆子的墓,与我父母的墓,相距不到百米。他说,这就是俺老婆子的墓。俺每天来这里放羊,像你一样,在她墓前坐几个小时,与她说说话。这个,他又指了一座坟墓说,是俺儿子的,死时才47岁,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去了。这个,他又指了一座坟墓说,这是俺父母的,死时都很年轻。就俺一人长寿,70好几了还不死。
我突然问了他一个未必合适的问题。我说,是不是人到您这样年岁了,就特别怕死?他哈哈一笑,说,别的人俺说不清,可俺一点怕都没有。俺这种人,财产没有,地位没有,亲人也没有,无牵无挂的。俺的牵挂都在这儿——他用手指指那几座坟墓。所有的亲人都在这里了。他说。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