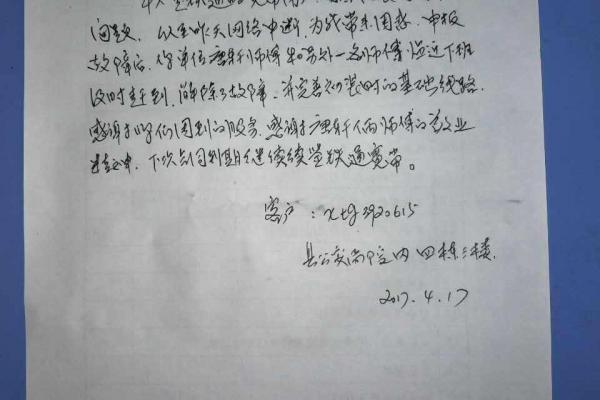我养了一株吊兰,叫小蓝,蓝色的蓝,不是兰花的兰。
去年秋天。我把连“株”都算不上的小蓝从它的母株身边带了出来,小蓝就这样从一“株”慢悠悠地长成了勉强可以称之为一“棵”的状态。栖息的方寸之地只是个可乐瓶底剪成的简易花盆,但她却乖巧地偏安一隅,飘在水里不声不响地缓慢抽枝长叶,全然一副无欲无求的佛家做派。
放假前我给小蓝加满了水,又在开宿后匆匆赶回,生怕盆里只剩个干瘪的细长叶片儿,套个塑封就能做成干吊兰书签。在扛着行李风风火火地冲进宿舍后,在阳台上见到了无精打采的躺在干涸的花盆里的小蓝,虽然我认为她生还的希望很渺茫,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拨下她完全枯干破碎的叶片和发黑的根须,换上一盆干净的水后轻轻地把她放了进去。
第二天,靠窗的室友们望着重新挺起腰杆支起叶片的小蓝,脸上出现了三个硕大的O型。
“我以为她都死了1
我也以为她都死了。
然而它又活过来了。带着冬末的虚弱和春初的生机,新根吮吸的水分如同脊椎之中流淌着的血液一般让它挺起了胸口,坚挺着每天拥抱第一缕晨光。
落叶,其实也发生在春天。停滞了一个冬天的时间被解冻,在风中发出如同干草一般哔剥之声的暮年叶片打着旋落入泥土和根茎之中,用垂死的声音唤醒沉眠的树木,睁开眼睛又是一片青葱摩挲。坚持走过冷酷无情的冬季困境,拥抱着的又是桃红柳绿的盎然生机。
我抚摸着小蓝叶片上还未完全愈合的伤痕,思忖着也许可以给它换一个大一些的花盆了。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