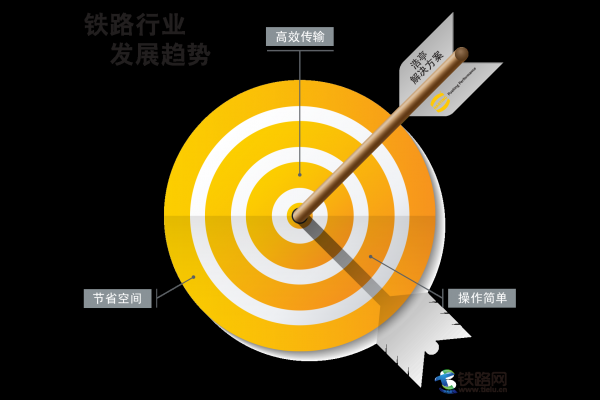芬妮/文
在铁路上,曾经众多铁路家属都拥有一个证件,叫“家属医疗证”,凭此证那些年在铁路医院就医可以半价,还可以和探亲票一起免费坐火车硬座。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家属证渐渐失去了它的作用,然而“铁路家属”的身份却让他们有着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人生。
给自己接生的女人
时间倒回到上个世纪的1963年的夏天。那一天,成都机务段火车司机付师傅准备出乘去内江接车,妻子钟兰英叫住了他:“你今天就不去了嘛,预产期都过了两天了。”付师傅沉思了一下,坚决地说:“不行,这个时候不好请假,各人有各人的车。”没有理会妻子的请求,付师傅去开水房打了两瓶水放进屋里,还是穿上工作服走了。
钟兰英是农村女子,那个时代,多数火车司机都是在农村老家娶了妻子再来开火车的,隔壁周立芳还有朱春梅,都是这样。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每年丈夫十五天的探亲假回来一趟,而妻子到单位去探亲,也只有探亲房提供十五天的住宿,然后就得收拾东西回家。
三年前,钟兰英将三岁大的儿子留在婆婆身边,到单位看望丈夫。不想一场急症夺去了儿子的生命。痛不欲生的钟兰英时时想起自己临走前那天早上,儿子端着一个装了两块红苕的小碗,哭着翻过高高的门槛追自己的场景。她如果知道那一别和儿子就是永别,一定不会把儿子留下。她下定决心,以后一定不会再扔下孩子。这次经过特别申请,单位上同意她住到孩子出生满月才走。她是想让孩子出生的第一眼能看到妈妈,也能看到爸爸。
此刻正下着大雨,屋檐上的雨水像瀑布般挂在眼前。钟兰英默默地看着丈夫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雨幕中,转身进屋,将孩子出生要穿的衣物一件件清理好放在枕头边,将准备好的瓷盆放在床边,将一个小闹钟放在了床头,用瓷杯倒了一杯开水放在床头的凳子上。晚饭时分,钟兰英感到肚子有些隐隐作痛,她知道孩子要生了。望着空无一人的小屋,钟兰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但她很快让自己镇定下来。她知道,今晚,只有靠自己了。
当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折磨着钟兰英时,钟兰英努力地挤压着自己的肚子,一声声唤着:“幺儿,快出来,不要折磨妈妈。”夏日的夜里,在这间窄小的房间里,一个女人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努力挣扎着、努力奔跑着,准备迎接他们的第一次相会。儿子终于在妈妈的声声呼唤中脱离母体,来到人间,来到母亲的眼前,此刻已经是午夜时分……
等钟兰英被敲门声惊醒时,已是早上八点过,外面的雨早停了。隔壁朱春梅推门进来,看见了躺在床上的母子俩,惊得瞪大了眼睛:“我的天!你怎么一个人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大晚上的,我没听到你叫呢?你太能干了,快点,你还没吃东西吧?我这就给你煮点吃的。”朱春梅边说边往外走,“周立芳,快点,快去给付师傅打电话,钟姐生了个儿子,叫他快回来。”朱春梅边说边找了几块砖头,在屋外的空地上搭了个简易的灶,将司机们打饭的饭盒放在上面,放了点水,煮了四个荷包蛋。这时,离钟兰英生下孩子已经有十个小时了。
付师傅赶回家已经是一天以后了,儿子终于还是没有第一眼就看到爸爸。多年以后,钟兰英已经变成了付婆婆。那次带着孩子回乡下后,她又连续生了一男两女。她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留在乡下,直到他们长大各奔东西。那个自己接生的儿子也如父亲所愿成了一名火车司机。
说到和丈夫三十年分居两地,付婆婆感慨地说:“铁路家属就是这样的,哪样苦不能吃?男人一年四季多数时间都在外面,哪能靠得了他?只有一切靠自己。”
等户口的铁路娃
七十年代开始,当火车驶过成昆铁路时,铁路沿线的小山坡上,时不时会有一排排盖着石棉瓦的简易平房,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周瑶和她的同学燕子以及小萌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长大。
周瑶的父亲是成昆线上某个火车站的上水工,三班倒。上白班时,晚上下班就是睡觉,上夜班后,白天又要留来睡觉养精神,妈妈在农贸市场摆水果摊,都照顾不到他们。她每天中午回家匆匆吃完饭,还要给妈妈送饭。周瑶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都在读书,中午放学他们分好工,哥哥姐姐负责做饭,她负责给妈妈送饭。为了贴补家用,他们还常常会在周末和假期,去批发一些水果、糕点,到站上叫卖。有时,他们也会到货场打点零工。哥哥帮着卸货,而她和两个姐姐就帮着装货,也能挣上十块八块的。那天,货场来了好几汽车西红柿,要马上装箱运出去。她姐仨从晚饭时分开始,一直干到凌晨,腰都累得直不起来了,终于把那三大车西红柿都装进了竹筐里,一共挣了25块钱,可把姐妹三人乐坏了。
可以说,当时整个铁路站区的家属都在干着类似的事情。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大批的铁路工人从成都平原和全国各地来到这大山里。众所周知成昆线气候恶劣,环境险要,曾有一句话概括了成昆线的天气,那就是:金江的太阳马道的风,燕岗打雷似炮轰,普雄下雨如过冬。
周瑶就是在这时被父亲拖家带口带到这个远没有自己家乡美丽的地方来的。父亲说,等户口转过来了,她就可以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招工和考技工校的待遇了。大批家在农村的铁路工人都怀着和周瑶父亲一样的想法,来到了成昆铁路的各个站段。
一家人在这并非城里但要城市户口的地方要吃穿住,得有钱得有住房。家属们开始充分利用地理条件,为自己弄一个遮风挡雨之所。于是,在铁路边上的一些空地上,一排排用石棉铺顶的简易平房就这样搭建起来了。那原本就是一些不毛之地,用多少地都没人管你。说起养家糊口,仅靠当铁路工人的这些爷们儿的工资,根本喂不饱家里的四五张嘴,得想办法挣钱。于是,在农贸市场,就多了一群摆摊卖水果的婆婆大娘;在站上,就多了一群卖盒饭、水果、面包的半大孩子,大一点的孩子还提着装有盒饭的篮子上车叫卖。生活,就这样在各种想方设法中依然过得有滋有味有盼头。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根据国家政策,这一大批铁路家属才陆续通过“农转非”,将户口迁到城里来,发了粮油本,成了正规吃国家口粮的城里人。
周瑶及班上的好几个同学最终都考上职高和铁路技校,而那些学习被耽误了的哥哥姐姐们,也名正言顺地参加了铁路的大批量招工;唐师傅45岁的妻子也被车务段招进了小集体,在车站站台推车卖食品。
多年以后,铁路家属们极富时代特色的“围车叫卖”和站台上推车叫卖以及车内提着篮子叫卖,已经为了安全而被明文禁止,货场的装卸工已是专业聘请,但那些铁路家属们为了生计,为了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做的点点滴滴,却成为铁路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作 者 手 记
爱的成全
在全国两百多万铁路职工中,有不少的铁二代、铁三代,甚至可能有了铁四代。真应了那句话:为铁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无论当初选择铁路是出于何种动机,任是谁这么多年与铁路朝夕相处下来,也一定是日久生情。在我童年甚至少年的记忆中,父亲都是身在远方的一个陌生人。父亲与母亲整整分居三十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是一个女人最美的年华。在一个女人最美的年华里,没有与爱人应有的相疼相惜,有的只是抚育子女的辛苦劳累。十七岁,我从乡下来到铁路边,从此以后,火车的轰隆声和鸣笛声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而身边那些为了生活天天起早贪黑的铁路家属,也让我看到了他们生活的辛苦。
参加工作后,作为我家的第二代铁路人,我再一次切身感受到了铁路家属的辛劳、隐忍与坚强。
如果说母亲那一代铁路家属的辛苦是时代造成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不少女性在职业能力上甚至超过了男性,她们选择放弃自己的事业,并非自己需要依附男人,而是因为她们那作为铁路职工的丈夫,为了铁路的发展而无暇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
如果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做出牺牲的女人,那么也可以说一个铁路职工的背后,大多有一个做出牺牲的家庭。
也许这些家属的付出或者牺牲,仅仅是出于对那个作为铁路职工的男人的爱,但正是因为他们不计回报的爱与成全,才得以让成千上万的铁路职工安心投入工作。
写此文,是想将记忆中那些曾经深深感动过自己的镜头呈现于大家眼前,想对所有铁路家属道一声:谢谢!
(芬妮)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