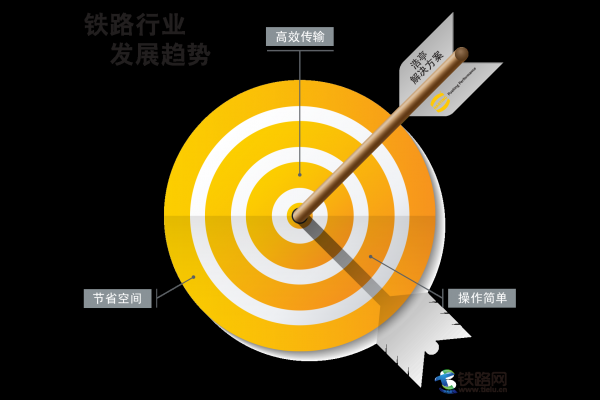韩玉皓
图一为已经废弃的铁道。
图二为中东铁路沿线保存完好的民居。
图三为螺旋展线群中的老建筑。
这是山里一段被废弃的铁路,从远方蜿蜒而来,穿过隧道,又继续伸进远方的雪野里,直到消失在视线之外。
隧道不长,视线穿过洞口,能清晰地看到对面的景色。我走进隧道,洞口处的钢轨在冬阳下闪着亮光,还没有那种锈蚀斑驳的迹象。隧道里的风很大,卷着雪花迎面扑来,我忙拉紧了风雪帽。脚下石砟的撞击声金属般回响,深深地击打着我的心灵,催促着我的脚步,穿越这时光隧道,阅读它的前世今生。
这里是中东铁路西部干线上最大的建筑工程——兴安岭隧道和盘旋而行的铁路线群。其主隧道位于滨洲线516公里262米处,出口洞壁上 “1901—1903”的数字清晰可见,证明它是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而贯通的,如今,已逾百年。
中东铁路哈满线 (哈尔滨至满洲里)由西向东过博克图小镇后,进入大兴安岭腹地。这里重峦叠嶂,峰岭相依,铁路只有形成螺旋展线、绕山而行后才能从东口进入兴安岭隧道,故当年在修建螺旋展线和兴安岭隧道的同时还凿筑了几个子隧道和连环隧道。我走的这个隧道,就是当时被称为 “兴安岭石头瓮道”的隧道。
随着铁路建设的长足发展,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输效率,2007年,滨洲铁路改线取直,螺旋展线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随后,当地政府将这个工业奇迹完整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今天的 “蒸汽时代”主题公园。
走出隧道,别有洞天。四周群山连绵,铁路环线盘绕。头顶之上,只有如洗的蓝天、飞过的鸟儿,脚下是一片茫茫雪野。
我们走进了高岗处的几栋俄式木刻楞建筑,尽管已经是残损破旧,但当年的风貌仍依稀可见。
“扑棱棱——”几只鸽子飞上屋顶。屋檐下,长长的冰溜子挂在那里,晶莹剔透。
我坐在屋前用旧枕木搭起的台阶上,身后是已缺损了房门的俄式老屋,眼前山谷里的 “天井”下,是废弃的铁路,还有当时留下的建筑、工事及后来修建的铁路建筑和设施。
我凝望着、沉思着,思绪穿越时空,想象着这里曾经发生或传说的一切:沙俄女工程师沙力因为担心兴安岭隧道设计出现问题、第二天不能如期开通,便于隧道开通前夜自寻短见。第二天,隧道贯通了,而且分毫不差,员工们欢呼雀跃;天真的孩子们穿着布拉吉、光着脚在这里追逐嬉戏,可设计者却长眠在了异国他乡。
这里既有传说,又记录着罪证。沙俄单方面把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掌控的伪满洲国政府,滨洲线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运输线。他们修筑工事,构建自己的生活与防御区。那碉堡四周黑洞洞的射击口,如今像一只只大眼睛在审视着什么,又似在传递着什么。掠夺、战争、和平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更迭交织着……鸽子的哨音,唤醒了我的沉思——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是记忆不可抹去。
迎着新中国成立的曙光,铁路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兴安岭隧道群中的新南沟站、沙力站、兴安岭站区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守卫者在这里贡献了青春,甚至是生命。
兴安岭隧道旁有个新南沟养路工区,出了个全国劳动模范张巨福。他巡道30年,至少走了6个半万里长征,管辖的线路从未发生过一起事故。他退休后,他的儿子、侄子接过他的道钉锤、巡检兜,成为了新一代岭上铁路养护人。
隧道前方的高岗上,曾经是部队的营房,如今已经封存。我们扒开一块积雪覆盖的石头,上面刻着 “走向哨位,就是走向战潮的字样,暗灰色的碉堡上标语的墨迹依稀可见。
我们沿着用旧钢轨和枕木搭成的 “天梯”,从谷底登上山腰。眺望铁路环线在崇山峻岭中穿行,我多么想再次看到这样的场景:蒸汽机车水满汽足,喷云吐雾,呼啸而来;汽笛声声,震荡山谷;车辆隆隆,排山倒海。那是一种何等的气魄与震撼埃
岭上的达子香花开花落,冰雪几度消融。从中东铁路、中长铁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铁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切都成为了历史。 “天井”之下,隧道之上,昨天和今天,历史与现实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盘旋而上的循环线群之间浓缩、凝结。是啊,山里有着无数条这样因完成了使命而被废弃的铁路,今天触摸着仍能感受到它们的温度。铁路废弃了,但是故事还在继续……
本文图片均由韩玉皓摄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