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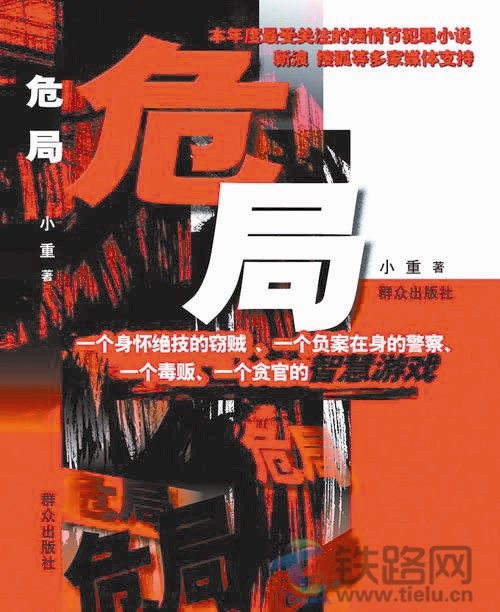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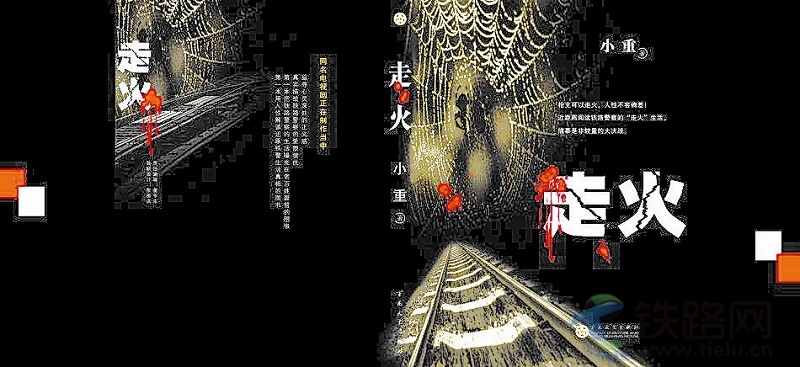
影,当时就知道看热闹,看人民警察如何智勇双全地虎穴擒敌,看公安民警怎么将潜伏的特务追得像野地的兔子满处乱窜,每到这时内心里总会萌生出一种冲动,长大了得当警察,最好还能用自己的笔书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这个念头像烙在身上的印记一般挥之不去,以至于在以后的很多年里这都成为我写作的动因。
现在偶然也会翻出以前的手稿,看着粗浅的描述和没有韵味的对话,自己能把自己逗得直乐。这也是我不愿意将它们扔掉的原因,好让这些不成功的稿件提醒着自己,走过的路不是一马平川。我也曾经在懵懂的状态里停留过,也曾经尝试过用多种方式来叙述故事,但总感觉缺乏将火热的生活转化成具有艺术魅力作品的能力。好在我从小养成了喜爱阅读的习惯,能让我通过各种刊物和图书汲取养分。尤其是在当兵的几年里,我沉浸在诸多域外警匪读物和国内反映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里不能自拔,从丰富多彩的文本里知道了作家陈建功、王亚平、丛维熙,也知道了公安作家海岩、张策、魏人、武和平等,阅读能让我与作家们共鸣,对我以后的创作生涯给予重要指导。
记者:公安题材小说,人物塑造是一个难题。怎样塑造一个符合时代审美的英雄人物形象,避免刻板和类型化,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心得?
李: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总是执拗地认为公安民警不是单一的颜色,英雄也不都是从天而降。他们可以是太阳折射下的七彩光,他们生活在这个与时俱进的年代,思想和行为不可能是老式的、刻板的、守旧的,而是在不断接触新鲜事物的同时,秉承着对职业的尊重、对法律的忠诚,怀着人性固有的执着和良善,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扬弃与自我完善,拥有人文情怀。基于这种思想,我笔下的人物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全”式的楷模,也不是胸怀广博放眼世界、站得高看得远的传统造型,而是我身边常常能接触到的那些有情有义,甚至有些毛病的民警哥们儿。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情,有自己的爱,有遭遇生活工作双方面压力时的一声叹息,也有面对邪恶黑暗勇往直前时的无所畏惧,更有兄弟情义两肋插刀时的披肝沥胆,他们是真正的平民英雄。
没有人情味儿的英雄是短命的,不懂儿女情长的英雄是平面化的,停留在虚拟方式上创作出来的人物肯定是经不起推敲的,也是立不住站不稳的。展现有文化氛围的警察群体,塑造有人情味儿的警察形象,描摹忠于法律忠于职业的平民英雄是我创作的动因。如何将这几点有机结合起来,并能成功地塑造出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是我在创作过程中始终追寻的方向。
记者:您认为好的公安题材作品应具备什么特质?
李:在反复的思考与探寻中,“细节”这个词被放大了,能支撑一部长篇小说延续下去的除了典型的人物形象、情节紧张的故事、娓娓动听的叙述语言外,细节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决定着文本的成败。而细节的来源,恰恰是写作者生活的积淀。这就需要作者将生活中相关的积累串联起来,做到合理铺排,有序安置。有的细节则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逐渐放大,起到衬托人物的作用。
记者:能否结合您的作品,为我们谈一谈您构思的过程?
李:在完成长篇小说《走火》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自己总会在梦中惊醒。因为在梦里我又随着刑警队的兄弟们,背着简单的行囊,顶着漫天的星斗,顺着拥挤的人流登上了夕发朝至的列车。他们都如影像般一个一个跳跃进我的脑海,跟我交流,与我坦诚相见毫无保留。他们俏皮的语言、睿智的思维、干练的举止、面对困难一往无前的勇气、面对罪犯除恶务尽的霸气,不停地撞击着我的神经,让我无法安稳入眠。
于是,我尝试着违背自己的写作规律,将要逃跑的贪官、凶残的毒贩子与保镖、新老两代贼王、闻讯来追杀贪官的杀手放置在同一趟列车里,同时为他们配备了相应的对手。如武惠民对于志明,鲁远航、周泉对毒贩子魏永仁及其保镖,朱得海对神偷老赶,窦智对杀手等。平心而论,这样写作的形式是要冒失败风险的。如此集中大密度地将众多人物聚集在一列封闭的列车里,并让他们产生关系,互为犄角互相牵制,互相制造麻烦引发故事,还要不留痕迹水到渠成,弄不好就会捉襟见肘仓促收官,这样的结果是写作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来,我克服了这一困难。
《危局》风驰电掣地带着我对警察职业的崇敬悄然上路。一路上我尝试着把写作的视野放开,把现实的记录放大,在深深地掘进生活的基础上将视角直接触及我所熟悉的铁路公安民警的最基层,聚焦到这一特定群体的特殊生活。我真实而又鲜活可信地反映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追求、他们履行职业“契约”的执着与忠诚、他们善良的心底、人性的光辉、正义的声音,还有他们几代人前赴后继用鲜血与生命铸就不死警魂、绘制无悔人生的炫丽篇章。同时我用老公安民警武惠民的艺术形象,向不计个人得失、奋战在公安保卫一线上的老民警们致敬。并以此告诉人们,在和平年代里的任何时候,都会有武惠民这样的公安民警,他们坚定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不被任何外界因素所动,不贪恋权力金钱和一切诱惑,真诚真实地履行自己朴素的职责,虽有千难万险至死不渝。
随着时间的推移,铁路公安系列作品的第三部《发现》也已经创作完成并发表。攀过几个山坡,留下几个足印,个中的辛酸与欢乐都已经深深浸透在我的文字里。我愿意在公安文学薪火相传的过程中做一簇火苗,用自己真诚的讲述燃烧,给读者和我的战友、兄弟们带来一丝温暖。
记者:对于很多从事公安题材创作的作家而言,金盾文学奖可望而不可及。作为一名普通的铁路公安民警,您如何登上各种文学奖项的领奖台?
李:文学奖项对我这个年轻的写作者是宽容和爱护的,并没有因为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基层民警而漠视我,也没有因为作品的稚嫩而舍弃我,更没有社会上种种评奖的暗箱,相反慷慨地将桂冠戴到我的头上。几年以后我有幸遇到当时的评委、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张策先生,聊起金盾文学奖,聊起《走火》获奖时,他的一句“你就是《走火》的作者呀”,才让我们第一次相互认识了对方。时间在不经意间慢慢地流逝,初次获奖后的喜悦也随之逐渐平息下来。“攻城掠地易,守疆拓土难。”获奖只是给这部作品画了个漂亮的圆,并不代表此后的文字都是优秀的。这个念头常常环绕在脑际,让我不得不收起骄傲,重新走回到书案前面,拿起笔继续为我的战友们写作,继续完成自己的梦想。
铁路公安是一个特殊的警种,多少年以来人们对此知之甚少。他们所付出的辛苦、流淌出来的血和汗也只停留在平面的宣传上,很少有人用文学的方式来记录他们。这就需要有一个群体,自觉为这个职业写作,而我就是这个群体里的一员。
记者:您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什么?
李:文学是让人感受到温暖的,文学是有力量的,文学是向善的,是净化人心的,是可以为他人打开暗黑的幕帘看到亮光的,是可以推动他人冲破厚重的墙垣找到通道的,文学可以给人呈现天地朗阔、山水坦荡。我不否认在某些现实面前,文学是无用的,但是文学可以提供精神价值,它教人学会悲悯与恩慈。我们用文学打开了一道道门,让我们看到一条条路。以后,在我们的文学创作里,我们自己也自觉地为他人打开一道道门,让人看到一条条路,看到曲水流觞,看到雪里红枝,看到萌生在天边的呼之欲出的朝阳。因此,无论艰辛与否我都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记得自己刚起步的时候,当时的铁路文联领导就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支持,为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提供了宽广的平台。很多机会是很多写作者可望不可及的,却偏偏落到我的头上,所以我说,自己是幸运的。在以后的时间里,我的每一个进步都有这些老师、兄长们的身影。就是因为有他们的助推和帮助,我才能走到今天,才会有今天的一点成绩。
说到目标,我没有确定的目标。我以前写过一篇短文,大概意思就是,自己是个行者,只有努力地向前跋涉,因为当我懒惰的时候,当我想放松下来的时候,好像总有个声音在提醒自己,别停下,路还长……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