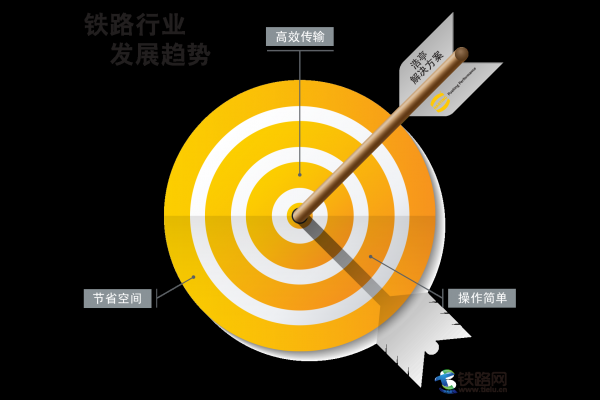——本报摄影记者曹宁的春运记忆
本报记者 荣倖
2月4日一大早,记者曹宁背着装有1台相机、3支镜头和1台笔记本电脑的双肩包,扛起一支三脚架,风风火火地向成都东站赶去。当天,2015年铁路春运正式拉开大幕,熟悉曹宁的人都知道,像这样的场合,一定少不了曹老和他的宝贝照相机。
这是曹宁以摄影记者身份参与的第33次春运。
有人说他是路局首屈一指的摄影大师,有人称他是《西南铁道报》的首席摄影记者,听到这样的称呼,他总是摆摆手说自己只是一个拍照片的记录者。从1982年进入《西南铁道报》以来,他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了西南铁路30多年来的发展变迁轨迹。
如果把曹宁拍摄的照片看作是一部西南铁路发展的编年史,那么翻阅这段历史会发现,他几乎每年都会用相当大的篇幅对同一主题进行浓墨重彩的刻画,这就是春运。“它不仅是我们铁路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也可以说是新春佳节来临前的信使,是人们一年到头时与亲人团圆的渴望,是中国人思念家乡的浓重情节。”在曹宁看来,“春运”两个字里包含的丰富内容,为他的照片赋予了超越工作层面的更深层次的人文意义。
在曹宁的办公室里,有4个大立柜,里面存放的全是他工作以来拍摄的照片和胶片。“这里面是我八九十年代拍摄的春运照片。”他从柜子中的一格抽出一只文件袋,轻轻打开,将照片铺在已经被各种报纸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的办公桌上。看着眼前有些微微泛黄的照片,关于春运的记忆涌上曹宁的心头。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刮向内陆,沿海地区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引发大量农民南下,寻求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农民工”一词开始在媒体上出现。“这是90年代初期的春运,成都站的广场上只能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曹宁指着几张密密麻麻几乎全是人的照片说。那个时候,为了记录下眼前这壮观的景象,曹宁从售票大厅大楼和候车大厅二楼的窗户翻出,蹲在大楼楼顶和雨棚上拍下了这些照片。
在曹宁的记忆里,那是一个一票难求的年代。为了买一张去北京、上海、广州的车票,人们裹着被子通宵达旦守在车站,售票厅排队买票的队伍从厅内延伸到厅外。车站为了提高效率,将行李房改设为临时售票点,但相对于人们对车票的巨大需求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
上世纪90年代前期,尽管铁路基础建设加快了发展的步伐,但愈加猛烈的南下打工潮让“人多票少”、“人多车少”的矛盾依旧突出。“那时候为抢一张票排两三天的队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即使买到票还不一定能上车,如果车上人太多,列车员只能请部分旅客下车等待下一班。”曹宁说。
他给记者翻出了一张旅客上车的照片:列车旁的站台前,黑压压一片全是涌动的人群,凝固的画面中,能够轻易分辨出人们对冲上列车的渴望。所有的人似乎都在找寻任何一个能够进入列车的缝隙,甚至包括车窗——一名男旅客半个身子已经塞进车窗,手上还紧紧抓住一个看起来不算轻的大麻布袋。让曹宁印象深刻的还有车内的景象:一排3人的硬座,通常挤了6个人,茶几上还坐着3个,过道也是挤满了旅客和行李,连脚都下不了地,人站着睡觉都不会倒。一次春运,曹宁在去广州的列车上采访,从这一个车厢走到相连的另一个车厢去拍照,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尽管是寒冷的2月,但等他挤到目的车厢的时候已是汗流浃背。“餐车工作人员送饭,是在列车停站时把送饭小车通过站台送到每个车厢。不夸张地说,最后一节车厢旅客要吃的中午饭要到吃晚饭的时间才能送到。”说起那时的场景,曹宁有些无奈。
“事实上,为了缓解运能紧张和买票难的状况,铁路部门一直在努力,各方面条件也在慢慢改善。”曹宁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运能限制,包括我局在内的全国各大铁路局,将装货物的棚车进行简单改造,在春运期间加开了字母“PDK”开头的棚代客列车,每节棚车车内安装了“卫生间”,专门在节前节后运送外出务工旅客。然而这也并非长久之计,1997年春运,我局取消“棚代客”,取而代之的是带有空调、软卧的“红皮车”。也是在90年代末,第一趟“红皮车”从成都发往厦门,皮质坐椅代替了木椅,自动保温水箱代替了塑料水瓶。90年代后半期,成都站广场上虽然旅客不减,但秩序明显有序起来。“广场增加了很多售票车,抽调更多的工作人员参与维护现场秩序,旅客分时段、分批次上车,”曹宁笑言,“那时候已经拍不到翻窗上车那样‘经典’的照片了。”
进入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铁路建设迅速发展,经过多次提速,中国迎来“高铁时代”。如今,高铁动车组列车、高铁动车组动卧列车的出现拓宽了“中国式春运”的回乡路;实名制购票、“12306”网上购票、自动售票机、电话订票等方式规范和改善了旅客的购票环境。这几年,曲线优美的新型动车、美丽优雅的“动妹”、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干净舒适的车内环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曹宁的镜头里。“去年底贵广高铁开通,今年春运,从广州返回贵州的旅客也能切身体会到高铁时代的便利了。”曹宁说。
相片虽然是凝固的瞬间,但却能清晰地反映历史的变迁。“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他一边说,一边将手中80年代的春运照片和笔记本电脑里去年的春运照片放在一起。相片里,拥挤的站台变得井然有序,破旧的绿皮车变成了曲线优美的白色CRH型动车,农民工手中的化肥袋变成了滚轮旅行箱。“一切都在变化。”曹宁说。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