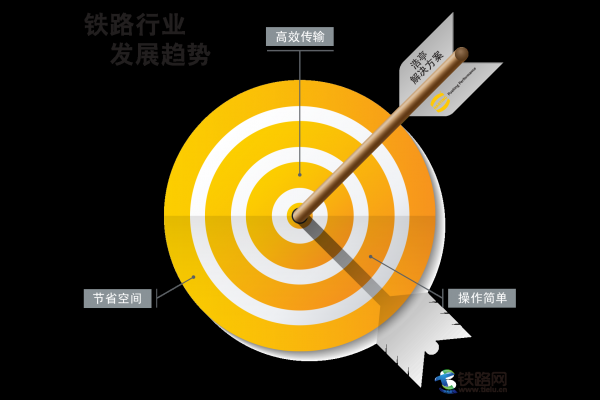阿坚
天又渐渐凉了,这个初冬应写些文字留给自己,因为立马退休转入吃饭拿钱的生活。于是清理办公室的物什便成当务。有的毫不犹豫就清除了;有的欲扔又放下,端详中回味良久,被它理出过逝的岁痕与遗迹。
有枚早已模糊不清的私章,柏木的,放在手掌轻如豆粒,是我插队落户第一个赶场日刻的,在生产队领口粮,去邮局取母亲的汇款,凡此种种,没这印章还真不行。当五年后办回城手续盖完最后一次私章时,公社秘书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好哇,要盖章领工资了。”原本要丢弃的私章才被我带回重庆,于每月20号去财务室从数十元到数百元盖戳多年,直至去提款机前取回工资奖金,我依然留着这小东西。这印章实在不起眼,却印证了我热血年华和养家度日的数十载光阴。倘若需要我初涉社会的实物标志,这枚长方形的印章便足矣。
卷宗里有一叠泛黄的纸片,展开一看,是些工资、职称、干部聘任的通知书,特别是20余张工资单,从40元人民币起步,一路攀升,足见芝麻开花之态势。这些破损的纸片,不经意间就在卷宗里躺了数十年,诠释着我与企业那一清二白的关系。我给它们拍了集体照,视为彼此的合影,从此不再联系。
卷宗里还有一叠纸片,是上世纪自己发表于各类报刊的散文随笔,刻意剪贴后标注时间将它们聚合一堆,这一沉睡又是十多年。此时浏览,一目十行,索然无味。恍若隔世的感受,让我决定不再保存它,于是一张一张揉成团丢进废纸篓。墙角的废纸篓渐次膨胀,像鼓圆的眼睛盯着我。这毕竟是一个业余作者的心血所获,尽管播种这精神食粮的季节早已过去,也谈不上硕果累累,却让自己乐享过,拥有一个个愉悦的白昼。我突感内心的些许残酷,冷漠自己也无情与此相关的人事。过去,我在一页页稿纸上写下所感所悟;现在,期望这些纸片变成纸浆,还原为一张张白纸。
桌上的这本《新华字典》,是1983年通讯员会议的赠物,数十年里办公桌换过多张,字典也修订多版,我对它却未动喜新厌旧之念,全系彼此的熟悉;就像大观园里的丫鬟,顺心顺手。尽管感情深厚,我也决然放弃它,因为这本字典于一位业余作者,可谓鞠躬尽瘁,去而无憾了。
这时候朋友圈发来一篇FT中文网的文章:大意是说繁体字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简体字使汉字的特质与意蕴消失殆尽,因为“简体字无法证明其存在的理由”。呼吁得有理,要恢复繁体字的大众书写却很难。这本新华字典与我共存了三十余年,简体字跟我们长大乃至终老,可谓积重难返;这也是读古文头痛的根源。
抽屉里还躺着一支老迈的英雄钢笔,虽无墨水,仍存英姿;还有几帧首日封……不再赘述,人一辈子要清理的东西,说多亦多,说少可屈指。
应有此想:我下一轮的清理,或许就别人来做了。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