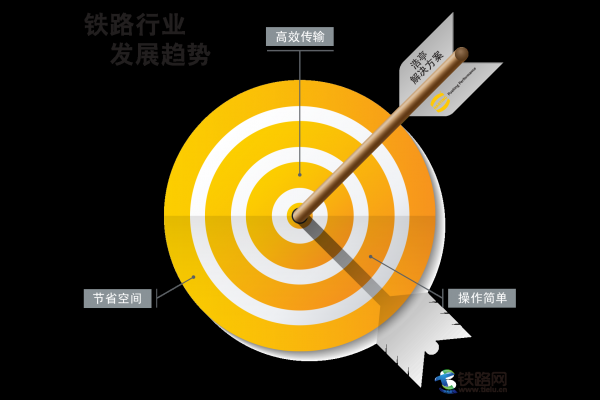“遥望家乡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我那可爱的小燕子, 可回了家门, 女儿有个小小心愿, 小小心愿, 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
70年代末,80年代初, 一曲《妈妈的吻》唱红了大江南北,打动了亿万听众的心。这是一首非常朴素动听,具有乡村人文情怀的好歌。
我就是听着这首歌,从军营到工程局,从南方到北方,四海为家。37年来,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那遥远的老母亲,我85岁高龄的老妈妈。一种思念之情,牵挂之爱,在我脑海里永远也挥之不去?
曾记得,在我记忆里,母亲常给我们兄弟仨说,我和你爸是晚年得子;三十岁才生了我,三十五岁才有了我二弟,四十岁生了我三弟。在我未出生前,我有个天真可爱的姐姐,可刚满六岁那年,不知是得了什么病,虽四处求医,可没等几个月就不幸病逝了;姐姐在离开人世时,拉着爸爸妈妈的手,甜甜地唱了一首儿歌。每当父母讲起这件往事,看得出我爸妈当时失去女儿悲痛的心情。人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现在想来,如果我大姐还健在的话,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时光飞逝,岁月匆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看似很漫长的路,却又是转眼的瞬间;回望37年来自己走过的路,既有骄傲、又有自豪、既有欣慰、也有遗憾,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尽的思念和牵挂,思念和牵挂我远在他方的老母亲……。
37年前的那一年,作为一名农村青年,最大的愿望和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和上大学,只有当兵和上大学才能跳出“农门”。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在那个年代,谁家的孩子去部队当兵,十里八村的父老乡亲为你高兴,为你骄傲和自豪。
我就是怀揣着这个梦想和希望,当上了一名铁道兵战士,那一年,我刚好十九岁。
在新兵连军训三个月里,我除参加严格的军训外,坚持每月向家人写一封家书,诉说衷肠,把自己参加军训、学习和工作上的事告诉千里之外,日夜牵挂的父母亲。每当两位老人读着儿子远在部队寄回去的家书,看了又看,多年也舍不得扔掉。
1981年春节的正月初五,服役三年的我,带着土特产从大连探亲休假。当我穿着绿色军装、头戴军帽走进家门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亲戚朋友把我团团围住,上下打量,问长问短。老爸拍打着我的肩膀,高兴地说到:“嗯,好小子,长高了,长黑了,像个当兵的!” “你在信上说,你们铁道兵修铁路、打隧道,干活累不累?怕不怕?苦不苦?好不好?”。站在我跟前的妈妈连珠炮似的一连向我提了好几个问题。“好!好!一切都很好!”我拉着妈妈的手,如数家珍地向父母和两个弟弟一一作了报告。
探亲休假20多天里,爸爸妈妈天天围在我的身边,陪着我串门走亲戚,给我煮好吃的腊肉、香肠,皮蛋……。把我当小孩子一样看待。吃着父母大人亲手做的家乡风味,甜蜜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现在想来,父亲母亲是多么的伟大,父爱母爱是多么的崇高和纯洁;在家的日子里,感觉是多么的温馨,多么的甜蜜。
1984年元月,兵改工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全国各地千家万户。当父母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逢人便说:我儿子当上一名铁路工人了。
看着已过天命之年的父母,望着二老花白的头发和一天天老去的背影,兵改工这一年的春节,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公社一名女青年,就是我现在的终身伴侣,相亲相爱一身的老婆。
我的婚姻具有戏剧性和喜剧性,从认识、谈恋爱到结婚,加在一起的时间刚好一个月,大家都说我俩是先结婚后恋爱。甚至有人担心我的婚姻基础不牢,是闪电式的婚姻,可实践证明,闪电式的婚姻也是幸福的、甜蜜的。
我结婚成家后不久便回到了内蒙古通霍线上。临走时,我拉着新婚妻子的手说到:父母年龄大了,我没有姊妹,两个弟弟还在上学读书,洗衣烧饭操持家务全靠你了。妻子含情脉脉地说到,你放心地去工作,家里不用你操心,我来到这个家,就是你的小妹妹…… 多么好的女人,多么好的妻子啊!
俗话说:“忠孝不能两全”。 37年来,我在工程局一干就是大半辈子;在父母面前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在妻子面前我不是一个好丈失,在儿子面前我更不是一个好爸爸。一句话,我没有尽到孝道和责任。
虽说我一、两年回家一次,甚至有时趁出差的机会也要回家看看,但毕竟假期短,每当告别父母和妻子、儿子时,感觉时间不够用,真想留在父母身边,陪陪他们,看看他们,哪怕只有一天。
1986年5月的一天,我怀孕九个多月的妻子快生产时,我借参加新闻培训班的机会回到了妻子的身边。不几天,妻子顺利地为我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一个家族有了传后人,父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从那天起,我的父母升级当上了爷爷、奶奶,身为人父的我,那高兴劲就甭提了。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本站观点。所转载内容之原创性、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